作者:张明扬,冰川研究员、新锐历史作家。
提及五代十国,大部分国人的印象只有两个字:乱世。
舍此之外,恐怕再没兴趣深入了解,甚至将五代十国当作中国历史的一段“垃圾时间”,毕竟——前承武德充沛的大唐,后启郁郁乎文哉的大宋。
所谓“垃圾时间”,不仅是不屑,也是厌恶。
五代十国当然是乱世,短短几十年间出了五个短命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然而乱世却未必就是“垃圾时间”。
我们为何要花时间探究这段历史?
五代十国对于当代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五代十国从何种意义上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偏好与观念世界?
01
五代十国参与定义了中国人的“乱世观”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段乱世,短的就不提了,长一点的有战国、三国、南北朝,化用葛剑雄先生的说法:分裂与乱世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当代中国人显然是极度反感分裂与乱世的,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观念发轫于何时?或者说,哪一段乱世最能触发近现代中国人的历史感?
我的答案是五代十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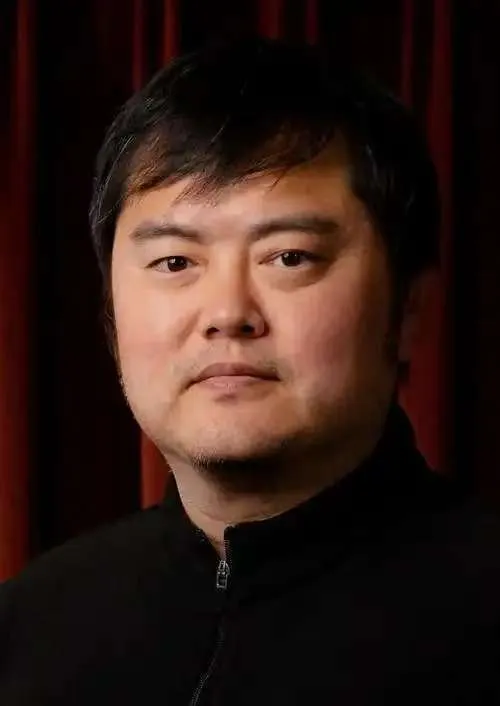
作者张明扬
论兵连祸结、流血盈野,五代未必比战国、三国、南北朝的程度更深,但偏偏就成了乱世的代名词。这和当下人对时间的感知有关系,毕竟五代十国是距今最近的长时段乱世,正所谓“殷鉴不远”;同时也和五代十国留下的“思想资源”有关系,比如,无论是在教科书里,还是在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传统认知中,关于乱世最有名的一句话恐怕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而这句名言就出自后晋军阀安重荣。
中国人虽然有“苛政猛于虎”的古训,但同时又认为“乱世猛于苛政”。五代,虽不见得有什么遗臭万年的苛政,但谁让你政权更迭得快,又有“十国”那么多割据政权呢?
这本身就是历史原罪。
南北朝那么乱,但东晋、宋、齐、梁、陈的易代速度看起来没五代那么快,因此显得更“稳定”一些。两相对比之下,五代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乱世。
何况五代还有那么多的“藩镇”!要知道,中国人可是将藩镇视为终结强大唐帝国的罪魁祸首!五代可以说是大大违背了中国人对大一统的历史信仰。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厌恶它厌恶谁?!
更不要说五代还丢掉了燕云十六州。南北朝虽然也有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叙事,但可能因为时代相隔太远,很难召唤起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而燕云十六州却不同,即使放在当代,它仍然算得上是中国人的历史隐痛,五代也由此更多了一条“失地”的罪过。
五代十国还被认定为缺乏英雄与英雄主义气质的时代。纵观中国历史,战国人物自不必说,赵武灵王、商鞅、苏秦、张仪、蔺相如、邹忌、庞涓、孙膑、白起、李牧、廉颇、诸子百家……哪个单拎出来都值得大书特书;三国更是英雄辈出,加上《三国演义》的渲染,简直成了“人类群星闪耀时”,几乎让我们忘记了三国竟也是乱世!即便是“黑暗的南北朝”,也不乏王导、祖逖、刘琨、谢安、桓温、王羲之等当下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
可五代十国又有谁?或许柴荣在中国人眼中算是一位英雄,但他不也没逃过“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命运终局吗?李煜,作为本书的主角之一,即使在文学史上如此熠熠生辉,还不是因为“治国无术”,就被当作和宋徽宗全无二致的昏聩之君?不知大家是有意还是无意,竟都遗忘了李煜做出的那些看似无意义却也倾尽所能的挣扎。
一个在国人眼中缺乏魅力的乱世,更容易成为乱世的典型代表。
以上几方面一结合,五代十国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乱世的“集大成者”。如果没有五代十国,中国人未必会如今日这般言乱世而色变。
02
五代十国参与塑造了中国人的“忠奸观”
在五代及之前,“君择臣,臣亦择君”是士大夫普遍的伦理观念,臣对君的“忠”不是一项无限责任,君主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以自号“长乐老”的冯道为例,他一生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仕于十一位皇帝(其中还包括辽太宗耶律德光)。然而他在当时却有着极高的政治声望,堪称“文臣第一人”。
冯道历史形象的逆转发生于北宋中期,由欧阳修与司马光联手将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新五代史》斥责冯道为“无廉耻者”;《资治通鉴》攻讦冯道为“奸臣之尤”。时至今日,冯道的历史形象仍然是负面的,甚至因那段出仕耶律德光的经历而被有些人目为“汉奸”。
更典型的是石敬瑭。
在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石敬瑭甘当“儿皇帝”,还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因而成为与吴三桂并列的两大“顶流”卖国贼(汉奸)。
石敬瑭虽然无耻,但“汉奸”这顶帽子他恐怕是担不起的。一来他是沙陀人,而非汉人;二来那个时代民族界限模糊,尚没有形成“民族国家”这个现代概念。然而,这并不妨碍石敬瑭被固化为负面的历史人物,他也很“荣幸”地成了当代民族主义的投射对象。
无论我们对这个时代多么无感和不屑,五代十国都已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论及北宋为何在当代如此受人爱重,除了其自身的灿若繁星,可能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原因—— 它终结了五代这个最为中国人厌恶的乱世。而北宋终结乱世的方式,也被“制造”成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南唐的亡国,被视作历史的“大势”,南唐的一切挣扎都被矮化成对历史潮流的盲目抵抗。李煜作为亡国之君,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被侮辱和嘲弄的对象。
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会惊奇地发现南唐本是南方第一大国,南方政权也并非天然比中原政权缺乏正统性。“中原中心主义”只是“见北不见南”的单线叙事,如李煜这样的失败者,则被历史或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
而吴越国的兴亡,从开国君主钱镠到末代君主钱俶,历经三代五王七十二年的辗转腾挪,也被粗暴地简化为“心向中原,时刻准备归附”的忠诚叙事。钱俶在宋太宗时代的“吴越归地”,被美化为顺应历史大势的主动归附,却无视他被宋太宗强行扣留、“人为刀俎,去国千里”的残酷境遇,更没人提“纳土归宋”后吴越国文武臣僚远在杭州的震天恸哭。
而北宋,它也不是这场历史记忆重塑中全然的胜利者。宋太宗兵败高梁河,与收复燕云十六州失之交臂。在当今互联网上,赵光义被讥讽为“高梁河车神”,连带他长兄赵匡胤“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都无法实现,整个北宋的历史形象也因此一落千丈……
历史,不能被“大势”湮没,失败者的沉默也如雷鸣般震耳欲聋。
本文为《卧榻之侧:赵匡胤、李煜和他们的时代》一书后记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