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叔河
文/唐小兵
题记:我要求的并不是怜悯,我要求的不过是(而且仅仅是)公正。(钟叔河)
友人王凯兄赠送了同乡前辈钟叔河先生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最新散文集《今夜谁家月最明》,读后感触良深。多年前曾经跟钟老有过数面之缘,那时候是因为知晓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全集》、《周作人散文全集》等对于文革后的中国文史界影响深远慕名而去拜访,对于钟老个人的人生却并不是太了解。多年后有机会读到导演、作家彭小莲和汪剑合写的《编辑钟叔河:纸上的纪录片》,才对于钟老的生命历程和学思才情有所了解,他在面对时代的重压和个人命运的翻转时,所展现的韧性和智慧,特别让我为之触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曾经是黑暗时代的受难者,也承受过来自周作人等人的人文主义的光泽,而到了文革结束,他以一己之力构建了一座人文主义的知识宝库,而面对波诡云橘的时代变幻,他将自我活成了“激变时代的燃灯者”和“人文主义的守夜人”。
真正的文史大家的人生态度,就如钟老在《今夜谁家月最明》写他在株洲洣江茶场劳改时认识的胡君里所言:“老实说,经历过四十年风雨的我们这一辈,苦都吃过不少,苦中作乐、先苦后乐的体验多少都有过一些,回味自然容易引起共鸣。要紧的是当以痛定思痛、推己及人的态度出之,勿作态,勿矫情,勿渲染,勿以为人间痛苦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别的人不是鬼子便是汉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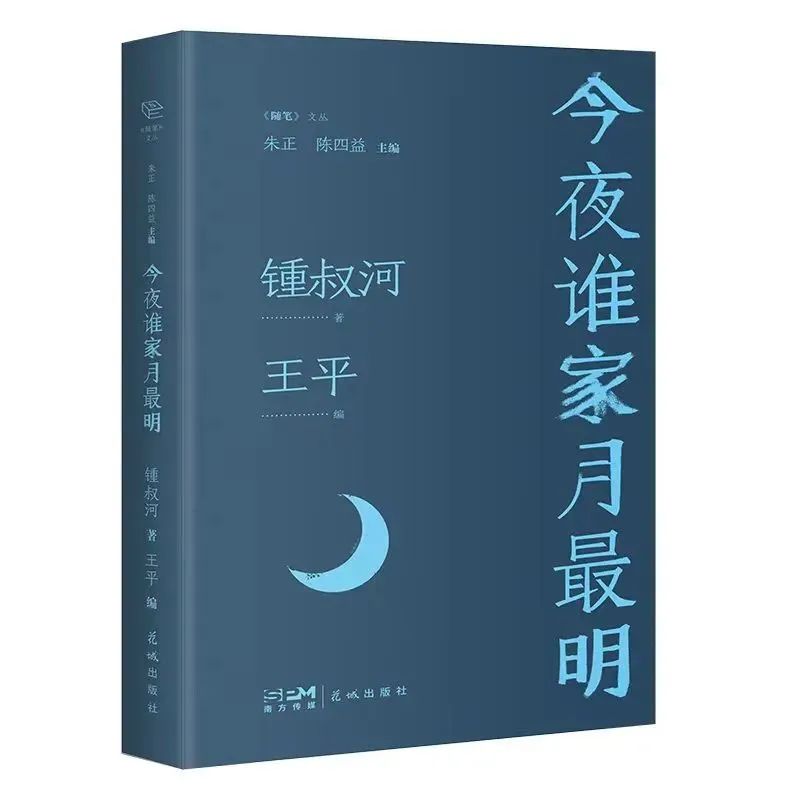
读钟老这本记述亲人、前辈和师友的散文集,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对于人间情义的看重和守护。韩钢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利益是刚性的,道义是柔性的。换言之,当道义碰上利益时,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趋利避害寻求自保甚至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像钟老这样至情至性之人,一辈子宁折不弯,坚持某种道德原则和知识诚实的准则活在这个人世间,避开宏大话语的碾压,而从细小的切口去领悟生命的真谛并将之化为普通人也可感通的文字,这就是一种人类丛林里极为罕见的“珍稀的物种”。
他在年纪轻轻风华正茂的时候从《新湖南报》被打成右派,回家自谋出路,在长沙的街头拖过板车,刻过钢板,画过图纸,为了养活四个女儿,他和夫人朱纯竭尽全力地活着,而且是“不抱怨、不诉苦”地活着,回到家面对嗷嗷待哺的女儿们,他坚持以微笑的态度化解生存的焦虑,家庭的小世界和小日子仍旧静水流深地绵延着一种高度政治化时代的难得的温情。数次访谈过钟老的汪剑如此写道:“一直悬在头顶的‘右派’阴云,超负荷的生存压力,与至亲的生离死别,每经历一次沉痛的打击,钟叔河和朱纯都必须以更加顽强的毅力站立起来,互相鼓励、搀扶,更努力地活下去,不仅仅在书页中寻找活下去的力量与希望,更是在这个狰狞冷漠的世界为着几分钱、几毛钱、几块钱胼手胝足地劳作,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努力生存,挺直腰杆,毫无惧色地活下去。”
阅读钟老的传记和他记人写事的散文集,盘桓在我脑海久久不散的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他走过那些无数黑暗、屈辱而痛苦的岁月?《编辑钟叔河》和《今夜谁家月最明》提示了两个最重要的脉络,那就是文化情怀和人间情义。
钟老是典型的湖南人,侠骨柔肠,一生重情重义,求真率性,不喜欢逢场作戏的虚伪,更讨厌曲学阿世的犬儒。无论是他写前辈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潘汉年、李一氓、罗章龙、张中行等,还是同辈朱正、黄永玉、李普等,或者晚辈王平、周实等,尤其是写父亲、妻子等的文章,所记述的交往和故事,都是那些长久地滋养和慰藉他的人生的场景和细节。钟老有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嫉恶如仇的个性,但同时也不乏楚地滋养出来的温情主义和率真情怀,从他这本散文集的字里行间,俯拾皆是的是他所在乎的人间情义。在他人生的天平上,真理和情义永远是第一位的,正由于有这样的价值准则,他在日常生活或大是大非等方面,都能保持价值上的一致和逻辑的自洽,说到底,他是一个虚伪时代的“真人”。
钟老在纪念同样出身于楚地的记者李普的文章中的这段话,何尝不是夫子自道:“能做到‘文章真有格’,就因为李普能一直保持他自己的‘书生意气’,这在同侪中是无与伦比的。书生即古之‘士’,‘士心曰志’。俗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书生只要有志,能坚持独立的意志,坚守内心的自由,培养浩然的正气,他就是坚不可摧的。另一方面,书生意气也会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出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钟老所认同的准则,也是支撑他数十年人生践履和文化实践的生命底色。就钟老而言,也就是充分地彰显了对人文和文化的重视。
他是相信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的。这在从曾国藩到沈从文到钟老、朱正先生等,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弦歌不辍的楚地精神传统,而其象征性文化空间就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岳麓书院。已故的同样身上流淌着楚地血脉的彭小莲洞悉了钟老精神世界的这一文化密码:“就是在尊严被剥夺的环境里,钟先生还是保留着对文化的热爱,这份热爱,支撑着他活下去。侮辱,是对‘犯人’最好的折磨,这成为监管他们这些人的职业。作为一个人,钟先生早就失去了价值,他是在残酷的威胁下、缝隙里,不断地为自己寻找最后的生存的‘意义’。靠着这一点文化,得到了救赎。这是真正的救赎,它不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找到自己灵魂的安放地。每一个字,都给钟先生悲惨命运带来营养,他依然活在自我的思想境界里。一个脆弱的个体,在面对着一个强大的、要陷害他们的社会和体制面前,终于存活下来。”
钟老这本文集题名为“今夜谁家月最明”,取自1960年代初与故人张志浩交往的一段往事。那时候,之前作为《新湖南报》同事又双双被打成右派的他们两人都刚刚摘掉右派帽子,没有正式工作,靠替大中学校誊刻讲义为生,刻一张钢板蜡纸可得六至八毛钱。1961年的中秋,张志浩带了一斤月饼来访,朱家孩子们吃完月饼后,他们闲谈片刻,钟老送张公步行回家。途经法国梧桐树发出沙沙声音的劳动路时,钟老感时忧世而倍感寂寥,这时张公却低声吟诗一首描摹其时场景和心境:“今夜谁家月最明,城南城北满秋声。长街灯尽归何处,萧瑟人间两步兵。”而发觉钟老心绪低沉,又做一首诗打气:“艰难生计费营谋,日刻金钢懒计酬。未必此生长碌碌,作诗相慰解君愁。”那是长夜跋涉中来自故交知己的心灵慰藉,长久地滋养着钟老的心灵。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他撰写此文时,钟老还如是感慨道:“在这三十五年中,张公这两首诗一直保存在我心间,无论是在月黑风高的长夜中,还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们都是这样的温暖,这样的鲜明。”
一想起钟老和朱正先生,就会觉得他们两个是湖南文史界前辈最有趣最博学的文化人,都有着有趣的灵魂。一本正经的道学先生往往让人生厌,满口时髦口令的人更让人恶心。钟老的人生恰恰彰显了胡适所言:“不降志,不辱身,不说时髦话,也不回避危险。”更为难得的是钟老表面上少年老成,但其实童心未泯,有着一颗赤子之心,这从他广博的文人趣味和元气淋漓的生命情调就可以管中窥豹。趣味和品味,也是判断一个读书人的气质雅俗的分界线,急功近利精于自售的人日积月累,往往面相狰狞而扭曲,而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超然物外的人,往往举手投足之间都浑然天成,毫不做作,言谈举止都自然生动。
钟老曾接受许知远主持的《十三邀》两次访问,那种热爱生命、崇尚自由和尊崇文化的气象,对于很多受众都有至深且远的感召力。一个即使活得再卑微的生命,即使低到尘埃里,仍旧有其不可剥夺的内在尊严和人格自主。在这样一个人类的至暗时刻,对于很多人都有治愈感,我们究竟怎样才能既有智慧也有韧性地度过这漫长的余生?钟老在评议同乡黄永玉的画时说道:“他的画法极新,却善写古意,多带装饰风格,色彩也很奇丽,而大笔淋漓,大气磅礴,表现出一种跨越古今的精神,也就是现代的精神。”而在评论王平的小说时,钟老也写出了一段妙语:“琐小的对面是伟大,流俗的对面是优雅。伟大应当尊重,优雅值得忻慕,但这得是从广泛的生活和悠久的历史中自然形成的伟大和优雅,做文章‘做’出来则未必。”

钟叔河部分著作书影
钟老对于曾经在暗夜中给予过他精神鼓励的周作人、钱钟书和潘汉年等人都长久怀着一份感激之情。他所巨细靡遗记录的与钱钟书、杨绛夫妇交往的细节,生动地彰显了文人之间的心灵契合和精神传导。在毛时代,苦闷中的钟老师费力搜集周作人的书籍,白天在长沙街头拉板车,夜里在灯下读周的各种作品。1963年深秋,钟老在给周作人的长信里的一段话其实也折射了他自己的写作和人生态度:“我一直私心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所最难得有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周作人应邀在回信中抄录了他很推崇的霭理斯的一段话:“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斯看来,似乎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黄子平先生认为霭理斯说的那支人文主义的火炬是传递到了钟老的手里和心里了,而他又通过编书、写书和言谈将这支火炬继续传递给中国的读书人。黄子平先生在为《编辑钟叔河》所撰写的序言《支离破碎的年代,一个完整的灵魂》中这段话最深刻地揭示了钟老的人格和取舍:“当权力与文化对峙的时候,钟先生选择站在文化一边。权力不仅没文化,而且蔑视文化,敌视文化。‘权力是没有灵魂的,而且它来自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丧失灵魂的基础上和从中汲取的力量,灵魂的阙失维持着和恐惧的联系……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他因此变成一个权力控制的范围之外的、真正的自由人。’”诚哉。
作者简介
唐小兵:学者,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
平台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授权微信首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