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发婚房
“订婚强奸案”的判决是个里程碑
文/维舟
“订婚强奸案”在山西大同宣判,二审维持原判:被告席某某以强奸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不亚于一堂法治课,因为它明确宣告:男女双方发生性关系,必须得到女性的知情同意,尊重其自主权。
此前,这一案件在舆论场上激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为被告叫屈的比比皆是,甚至倒是更占上风,其辩护策略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种:
一是辩称“双方没发生什么”,因而也就不是强奸。2024年1月,《华商报》采访被告父母的报道中提到,“按儿子的说法,案发时双方自行脱掉衣服,之后没有实质性性行为”。
比这种个人说法更精巧的一种类似辩护策略,则坚称“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什么”,核心证据不足以证明性行为发生过,因而秉持“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原则,男方不应被判罪。
二是宣称“虽然发生了点什么,但那是彼此自愿的亲密接触”,所以也不是强奸。被告的父亲曾在网上发文称:
5月2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当天中午,女方家宴请我儿子,饭后两人回到婚房。我儿子说,他们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有了亲密接触绝非强奸,而且开始进入电梯的视频也是表现的非常亲密,但女方却报警称被强奸,一审法院判处我儿子有期徒刑3年。
与之相似的一种说法,认为“虽然发生了点什么,但已经订婚/同居了,所以不算强奸”,网上诸如“双方当事人为同居关系”这样的传言,就是如此,这种说法暗示,女方其实早就默许了,即便当时没有明确的自愿,但两人的关系已经使女方“事实上自愿了”。
三是影射女方诬告,不存在强奸事实,只是她个人品德有问题,财产利益未得到满足,试图以控告强奸来达成个人目的。网上盛传的“骗婚”、“以告强奸进行敲诈”、“订婚发生关系后第4天,女孩控告强奸”、“女方有过婚姻史”等谣传,均属此类。
第一类已被证否,审判长明确指出:“本案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认定席某某强奸被害人的事实。”既然如此,那么第三类也可以被驳倒,因为这就不是诬告了——严格来说,这类谣传才是诬告,这甚至根本不是一种辩护策略,因为女方品德如何,并不能证否被告清白无辜。
比较棘手的是第二类,也是争论的焦点,即女方是否自愿?审判长的回答是否定的,并强调订婚并不使男方自动获得性权利,呼吁用法治思维破除“订婚就有性权利”、“彩礼捆绑权利”等错误观念:
与妇女发生性行为不能违背其意志,与双方是否订婚没有关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该罪侵犯的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妇女按照自己意志决定自己性行为的权利。因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犯罪构成的关键要素。

涉案双方的订婚书
之所以说这一判决是里程碑,因为从社会的种种反应来看,这种“发生性关系不得违背女性意愿,必须获得其知情同意”的观念远未深入人心。
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因为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女性一直缺乏充分的身体自主权。
传统婚姻的缔结双方并非新郎新娘本人,而是其家长,女性既不能自主选择婚配对象,其个人同意对婚内性行为也无关紧要。苏成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这种性行为的正当与否并不取决于女性的同意或自愿参与:
妻子的同意并不是正当的性交行为的前提。事实上,支配婚姻的那些规范要求妻子须顺从其夫,正如同它们要求丈夫须在道德上对妻子加以教导。因此,若丈夫强迫其妻与自己性交,则此行为并不属于“奸”的范围。
事实上,当时社会普遍认定顺从丈夫的求欢与其圆房是对妻子最基本的要求,“倘若女性想取消她自己不愿接受的婚姻,则拒绝圆房是最好(可能也是唯一)的策略”,即便缔结婚姻并未顾及她个人意愿,她也无权反悔,因为妻子这一法律身份就界定了女方的义务和男方的权力,她“摆脱这桩交易的唯一途径,便是迫使她的那位新丈夫将其退回去”。
明代也有律条规定:“男女订婚未曾过门,私下通奸,比依子孙违犯教令律,杖一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尊重女性权利,因为这无论双方自愿与否都要受罚,处罚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一行为无视家长的权威,擅自过早发生性行为。
乾隆七年(1742),一名童养媳被旌表为守贞烈女。其未婚夫企图提早与她圆房,她奋力抵抗,命丧当场。朝廷在旌表她的圣旨中,赞许她拒绝“夫之私欲”,表现出“以礼自持”的贞洁。也就是说,重点不是其个人意愿,恰恰相反,她的“守礼”意味着对父母权威的顺从优先于对其未来夫婿的顺从,因为父母尚未正式同意他们圆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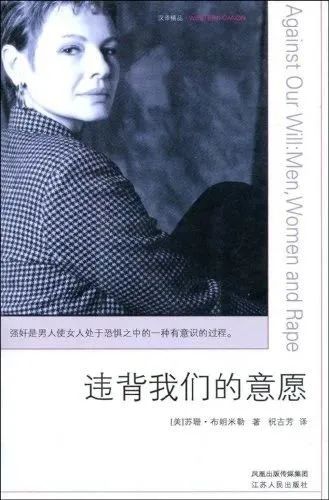
《违背我们的意愿》
[美] 苏珊·布朗米勒 著,祝吉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6-4
我们现在对“强奸”犯罪的理解,实际上源于西方。正如苏成捷指出的:
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强奸及其他暴行之所以被界定为犯罪,是因为此类行为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但是,这种释义方式预设了,此类犯罪行为所侵犯的,乃是个人拥有的自主支配其身体的自由意志。
正因此,一部研究强奸问题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就题为《违背我们的意愿》,从女性自主权和主体性受侵犯的角度来看待:“强奸是男人使女人处于恐惧之中的一种有意识的过程。”
西方的法律传统从古罗马时期起,就主张正当婚姻的最基本前提是新郎新娘双方的“自主同意”(free consent),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法庭极大地强化了这一信条,将婚姻界定为两个平等的灵魂基于其各自的自由意志在上帝面前举行的圣礼,“自主同意”因此成为现代契约法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
讽刺的是,正因为女性是自主结婚的,西方法律规范才出现了“婚内豁免权”(marital exemption)这一概念,理由是:既然女性进入婚姻必须出于自愿,那么夫妻双方一旦结合,就相互负有为对方提供性服务的婚姻义务,不能拒绝履行。也就是说,女性身为妻子无法主张“未表示同意”,那么“婚内强奸”看起来就是一个矛盾修辞。
顺着这些历史脉络来看,现代中国的女性可以说身处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社会对婚姻的理解原本就缺乏对女性个人权利的保障、自主意愿的尊重;另一方面,虽然现代婚姻也着重双方的自主同意,但有的是人相信,女性只要订婚、接受彩礼,就已经是“同意”了,从而自动丧失了身体自主权。
正如我一位女性朋友犀利讽刺的:“有相当比例的男性认为,女性只要答应跟自己吃饭=答应跟自己上床;答应跟自己去旅游=答应跟自己上床;同意自己去她家=同意跟自己上床。”
韩寒的名言应该代表了普遍的男权文化里的男性性别认知:女的答应跟你约会吃饭,就说明可以上床了。甚至不乏有男性自信地认为,女性嘴上说“不”,其实是在同意。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和个人意愿很难得到充分尊重。有一次,一位姐姐说:“在场的女性如果有谁能发自内心确信自己发生的每一次性关系都是纯粹自愿的,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以举一下手。”然后无人举手。
社会意识的变迁往往是极为缓慢的,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信奉的理念,与法律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就在当下,仍有许多地方的人普遍认为“办酒就是结婚”,我一对朋友办酒之后多年都未领证,双方父母竟然一直没意识到他们在法律意义上其实并未结婚。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次“订婚强奸案”引发的争论,固然让当事受害者承受了不小压力,但对社会进步来说意义重大。判决以法律形式明确裁决:订婚并不等于女方同意发生性关系,其个人意愿必须得到尊重。
既然如此,那么婚内呢?妻子的个人意愿就可以被违背了吗?
作者:维舟,书评人、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小说《无岸之岛》、评论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原载公号“维舟”,经授权转载。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