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x的成功故事
文/海北尬生
星舰在前几天完成了第10次试飞,完成了所有的既定目标,是一次空前的大成功。昨天在七维发了一篇关于俄乌战争中观点的文章那些希望乌克兰出个汪精卫的人是什么脑回路,结果立即有人在评论区里点名让我写星舰第10次试飞,也可见这事的关注度。
我当然是要写的,不过首先请大家理解,我们公号发文章大致都是在每天早上6:00 7:00左右,这个时间不可能赶上当天的星舰试飞,因此都只能放到第2天才发表,需要稍微等一等。当然对于写作者我而言,这个话题也很难写:能写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又要尽量把事情讲得简洁易懂。但是还是那句话,我怎么可能不写,这是我的专业啊。
我不太清楚读者是怎么评价马斯克这个人的,最近几个月里他和特朗普从好到穿一条裤子都不显瘦到彻底闹掰,恐怕也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同时他与人交往向来有问题,说话不管不顾,再加上对生育问题的“过于开明”,也惹出了不少麻烦。但至少他的专业素质是过硬的,航天界没有什么人敢在这方面质疑他,类似的,汽车行业也往往不在这方面质疑他的特斯拉。
必须要承认马斯克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工科生。当然作为企业的大老板,他不会亲自去设计细节的东西,他的任务在于抓方针,抓战略,抓技术路线,而他抓的技术路线往往都是正确的,比如特斯拉的热泵系统,再比如space x的各种决策,我们会稍后细说。
当然正像所有取得成功的人一样,他对自己的梦想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执着。早在零几年的时候,他就把火星当成了自己的梦想,一直坚持到今天,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洋典范”。目前所能找到的他对于火星的第1个任务规划,是01年的事儿。他的想法是,往火星发射一个带有植物种子的温室,在火星环境下观察植物的生长,为未来建设火星基地提供数据支持,这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性的任务。没有运载火箭,他就打算买俄罗斯退役下来的弹道导弹。导弹能提供的运载力当然有限,他真正要送到火星的温室只有一个篮球左右大。
相较于今天的space x火星任务,这样的任务绝对是寒酸至极的,但就算如此马斯克也展露出了自己的能力:比如试图购买退役的俄罗斯导弹当运载火箭,这体现了他充分利用既有产品和技术,以及压低成本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和方法被他一直坚持到今天。正是因为如此,他的这篇报告被获准参加01年的火星学会年会,初试啼声便不同凡响(当然这个学会也邀请过我)。
彼时马斯克的pay pal刚刚被收购,他也把自己的家产提升到了10亿美元的程度,但是这点钱投进航天项目的汪洋大海里都不会有一个响。人们都不看好他,觉得这个人有热情,但也只是仅此而已。他的那些想法过于大胆,也往往都很离经叛道,再加上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航天专家,而是一个it工作者,一个码农,于是就更遭到了人们的冷眼和鄙视。
在做完报告差不多一年以后,他成立了space x,而且最初口气就不小:他试图把航天做成一个能盈利的生意。当然他并不是第1个做航天的民营企业—美国的航天一直是依赖企业来进行生产的,也有像ula这样的公司试图做发射,但这样的公司首先是背靠波音、洛马这样的大巨头,其次也是靠和政府的深度合作特别是靠补贴来维持自己的运营。马斯克作为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老板,搞不到这么多的补贴,就只能寄希望于让火箭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到这儿事情还可以理解,但是他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他希望能够实现彻底的盈利,这也就意味着,每次发射火箭的设计、生产、发射成本等等,加合起来必须要小于客户支付的费用。
想做到这一点,路线其实也早都有,那就是要实现火箭的回收:花几亿造出来的火箭只能是一次性的,这样当然不可能盈利。火箭回收的方案很多,钱学森先生六十年代的名著《星际航行概论》就提到好几种,包括著名的航天飞机其实也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马斯克最初在猎鹰1号上选择了用降落伞回收第1级的方案,这也是经典的老概念,但他很快他就发现这与其他的回收方法一样都有严重的问题:技术上可行,但经济上不可行。火箭回收的成本、回收回来后整修的成本加到一起其实是要大于一次性的火箭的。包括美国的航天飞机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在猎鹰1号结束使命,他们开始研究猎鹰9号的时候,马斯克开始放大招:他要用垂直回收,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当然,这也不是他的原创,早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方案,美国和苏联都有。只不过双方的国家队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个东西理论上可行,实践层面却难度很大,于是就不约而同的将之束之高阁。马斯克这时做过的最大的火箭也是只有20多米长的猎鹰1号,在专家来看还很稚嫩、青涩,业界的不看好也就可想而知。(至今都有些人说马斯克在发展过程中NASA起了很大的帮助,实际上这就是酸葡萄:且不说NASA根本不会支持一个他们不看好的项目,要是NASA这么神通广大,他们怎么没造出自己的星舰、自己的可重复利用火箭来呢?)
但这时马斯克在IT行业积累的经验发挥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回收的过程中涉及到复杂的动力学和控制问题,但是这恰恰能发挥马斯克和他手底下这些计算机方面的人才的作用,通过大量的数值计算和仿真,马斯克的团队成功找到了控制火箭的方法。而且数值计算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研发成本极低,因为不需要真的做实验,同时周期也很快。当然想要做好它难度还是很大的,但是对于马斯克这些程序员出身的人,事情也不那么难。
此时另外一个问题到来:控制这样的火箭的程序的复杂程度远超过既有的火箭,于是对计算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火箭用的计算机计算性能都很差。这里多说一句,火箭的计算机要花相当大的精力来对抗宇宙射线的轰击,高能的宇宙粒子打到芯片的晶体管上,是可以造成比特翻转的灾难性的后果的,也就是原本算出来结果是0,却变成1,或者反过来。于是通常情况下给火箭和飞船设计的计算机都着重考虑防辐射性能,甚至还会用电子管,而不是晶体管,因为电子管的抗干扰能力更好。这样带来的副作用就是,火箭和飞船用的计算机速度都非常慢,比如联盟号用的阿尔贡16计算机速度就只有5赫兹,中国空间站的主计算机时钟频率只有10兆赫,内存也只有2M,只能存一张照片。但是这样的计算机也价格不菲,单位都是亿元。
马斯克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答曰,他直接购买市场上的成品芯片(主要是英伟达和英特尔的产品)。那么比特翻转怎么解决呢?答曰,他同时联用好多个芯片一起算。因为很多个芯片一起算出问题其实是小概率事件,一起算出同一个错误答案就更小概率了,所以只要选取这些芯片算出来的最一致的那个答案,就可以保证结果是正确的。
比如space x的初代龙飞船,飞控主计算机由三台完全一样的计算机组成,每台计算机用的都是双核的芯片,实际运用过程中每个核单独使用,于是输入同一个数据后可以得到6个独立的答案。每一步计算完成后,每个核之间都会比对数据,执行多数的答案,也就是说即使某一个核某一步算错了,也会从其他核那里获得正确答案,再继续算下去。其他系统也是如此,最后一个初代龙飞船上要装54台一样的双核处理器。猎鹰9号火箭也是如此,每一个火箭发动机的控制单元都有三台这样的处理器,9台发动机加起来就是27台,同样飞控主计算机也是三台处理器,每一个也都是双核的。
民用的芯片相较于国家队的产品,首先是价格极其低廉——一个飞控主计算机系统总共才值2.6万美元。而且民用的芯片相较于传统芯片,在运算速度上能查出好几个量级,于是space x用来回收火箭的复杂程序,也不用再愁算力了。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解决方案,着实让国家队有点尴尬。我还记得某次某院士出去介绍他们研究的航天用飞控计算机,结果被懂行的听众问到space x的这个方案,很尴尬地被挂了黑板。
诸如这样简单粗暴,但又能一箭双雕甚至多雕的方案在他们那里真是不胜枚举,也恰恰是这样的方案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再举两个例子:
Spacex的发动机是非常好的,但这个好并不体现在推力上,而是体现在经济性(星舰的一台发动机只用20万美元)和效率上。若论推力,他们的所有发动机都只是中档水平。为了提供足够的推力,他们多发联用,比如猎鹰9号一级联用9台(猎鹰9号的9就是这么来的),重型猎鹰将三个猎鹰9号的一级捆绑起来,相当于是一级有27台发动机,星舰一级联用33台。
对于某些老学究和业余人士而言,这样的设计简直是离经叛道,他们是不敢连着用30多台发动机的,毕竟苏联的n1火箭就栽到了这个方面,顺带着毁了苏联的登月计划,我也写过这个的文章航空航天是对抗的最前沿,也是友谊和平的急先锋。换言之,他们觉得多大的火箭就要用多大的发动机,星舰这种最大的火箭,就应该用推力最大的火箭发动机。
N1火箭的失败当然是一个惨痛的例子,但只能说这些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N1火箭多发联用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时间过于仓促,没有解决好燃料供应、振动等多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程序过于复杂,超过当时的计算机的水平,可是这些问题对于space x而言早都已经被规避掉了。振动之类的问题。通过仿真、模拟就可以很好的解决,Space x他们就擅长这个,至于计算机,上面也提到过。而且space x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星舰装33台发动机,看起来很突兀,但是他们之前设计的重型猎鹰一级已经用了27台发动机,量变已经不足以引起质变了。星舰的10试飞有成功有失败,但没有一次是由多发联用而起。

spacex 图源网络
问题不存在,剩下的便都是好处:首先是这样的发动机需求量大,产量大,于是就可以更好的平衡、降低成本,同时这也更进一步方便了他们的垂直回收方案,因为火箭返回着陆时基本上是空的,重量很轻,所需要的推力其实不大,spacex他们可以通过只启动部分发动机,实现更小的推力,比如猎鹰9号返回时只启动中间一台,星舰返回时只启动中间三台,也就是说只产生相当于起飞时1/10的推力。而如果采用的是更大的发动机就做不到,火箭发动机往往只能节流到最大推力的60%左右,再低就不能正常工作,就如同汽车发动机怠速的时候都要最起码600转一样。因此这是一个大智若愚的方案。
另外一个例子则是星舰用的材料。众所周知,星舰是不锈钢的,这在整个航空航天界都是前无古人的。当然,这并不是马斯克的最初选择,他最初也打算用又轻又时髦的碳纤维,甚至还为这个专门收购了一家做碳纤维的公司,但最终还是很干脆的回到了不锈钢上。为什么是这样?这也是非常巧妙的工程学设计。
首先星舰是一艘要返回地球的飞船,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应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热的袭击,而不锈钢的好处就在于它在高温下的强度更高:不锈钢可以在600多度的温度下仍然保持强度,但如果是铝合金或者碳纤维,却只能忍受200多度。所以碳纤维和铝合金当然可以减重,但最终需要更多的隔热防热的设计,站在总体的层面来看,实际上是把通过换材料省下来的重量又在隔热材料上加了回来。
其次,不锈钢也极其好加工,这一点碳纤维钛合金就比不上。碳纤维材料如果发现有裂缝,修补起来是很繁琐的,钛合金的焊接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因为它熔点实在是太高,但如果是不锈钢,事情就很简单。当其他的火箭需要在无尘的作业间里用等离子者摩擦搅拌焊接,或者用铺带机慢慢铺带的时候,Space x的团队却敢在半露天甚至露天的厂房里直接开焊,既省钱又省时。
当然最明显的,不锈钢便宜,便宜至极。迄今为止,星舰进行了10次试飞,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之前还建了十来艘地面实验用的飞船。这如果是传统的项目,到这里会直接崩溃掉,因为开支已经失控,根本不可能只是单纯为了做实验、搞迭代就造出20来个飞船,但是马斯克他们不怕,因为他们的火箭实在是太便宜,扔了就扔了,炸了也就炸了。这里面其实也有他们软件工程师式的思路:软件工程师往往可以边测试边迭代,不要求一次就交出最后的成品。现在他们在硬件方面也敢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高度模块化的设计很容易替换,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迭代,其实没什么可怕的成本。整个星舰项目每年总共只有20亿美元左右的现金流,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典范。
当然还有一些很聪明的设计就不详细展开了(比如用筷子夹火箭,可以省下着陆支架的重量)。总而言之,马斯克和他的团队确实能找出最简明最高效的设计方案,也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技术,更能够降低成本。他们给传统的行业从业者带来的震撼往往不是技术层面,而是观念层面,他们真的是在用一种六七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做着航天。
比如说火星学会那次我就遇到了猎户座飞船的总设计师胡先生(此人真的姓胡,名叫霍华德胡,也真的是华裔),他就很坦诚的跟我说“Space x的架构比我们好,他们的团队紧凑而高效”。中国的同行也大致是这样的看法,实际上这事儿是可以公开说的,比如说某单位就在他们的公号里推了这样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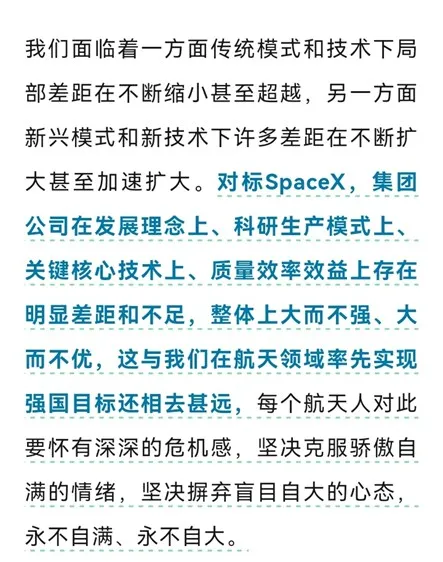
他们确实应该有危机感,因为马斯克的团队总共才六七千人,中国的航天却30多倍于此,得到的支持更远非马斯克所能比,可是偏偏星舰、星链这样的产品却出自马斯克那里。如果真说要改,我觉得恐怕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种文化。
中国的学生往往都知道,不要随便去驳导师的观点,哪怕你的是有道理的;那进了企业和单位,也都知道不要随便去驳“某某总”“某某院士”的方案,往往只要他们开了口拍了板,就去做就好。但是在spacex也好,特斯拉也好,什么方案都可以去驳,哪怕是马斯克本人拍板的方案,只要你能够详细的有理有据的论证出你的方案比他更好,照样是会受到奖励和提升乃至重用的。比如说星舰的材料问题,最初选择碳纤维就是马斯克拍的板,收购那家做碳纤维的公司,当然更是他的行动。就当万事俱备的时候,突然间出来一个人详细计算了使用不锈钢的数据,于是他们真的把马斯克“钦定”的方案推倒重来。这样,他们真的是发挥了群众的智慧,而我们在方案层面往往只是那么特定几个人的意见。
总结一下就是,Space x的成功是很多方面的,在他们离经叛道的设计思路和非专业的出身和组织架构的表面下,其实藏着对工程的深刻理解和其他同行难以企及的雄心壮志。成功归成功,他们毕竟搞的是技术而不是巫术,是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学习的。他们能做到,我也并非做不到。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