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远未消逝的过去
——读纳粹德国的历史有感
一
我一直对德国19世纪中期以后的历史很感兴趣。不只是因为我所从事的刑法学专业,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深受德国法学理论的影响,而这样的渊源要回溯至清末五大臣考察各国而得出“师法德日”的判断;也不只是因为纳粹德国时期法律界人士(包括实务界与法学界)大多都支持纳粹政权或者至少是亲纳粹的力量,这一点始终让我难以置信而困惑不已;更是因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在过程中不仅给其他民族造成巨大的浩劫,也给本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纳粹德国的出现,究竟是德国文化与制度本身所导致,还是内在于欧洲的文化基因之中,抑或是现代性自身的顽疾,对于这个问题,我迄今还未找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
前段时间看完的《大清算》([英]玛丽·弗尔布鲁克:《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陶泽慧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版)一书,以细致入微的笔调,将个体经历置于宏大框架中,来讲述国家支持的系统性暴力,如何让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德国人以施暴者或施暴者的支持力量的面目出现,对另外数以百万计的群体(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残障人士与同性恋者等)采取工业化的方式进行灭绝,而二战后无论是当时的东德还是西德,都没能对纳粹与亲纳粹的力量进行系统深入的清算。用刑法来清算国家支持的系统性暴力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这样的暴力并不单纯是犯罪问题,但人们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有效地清算纳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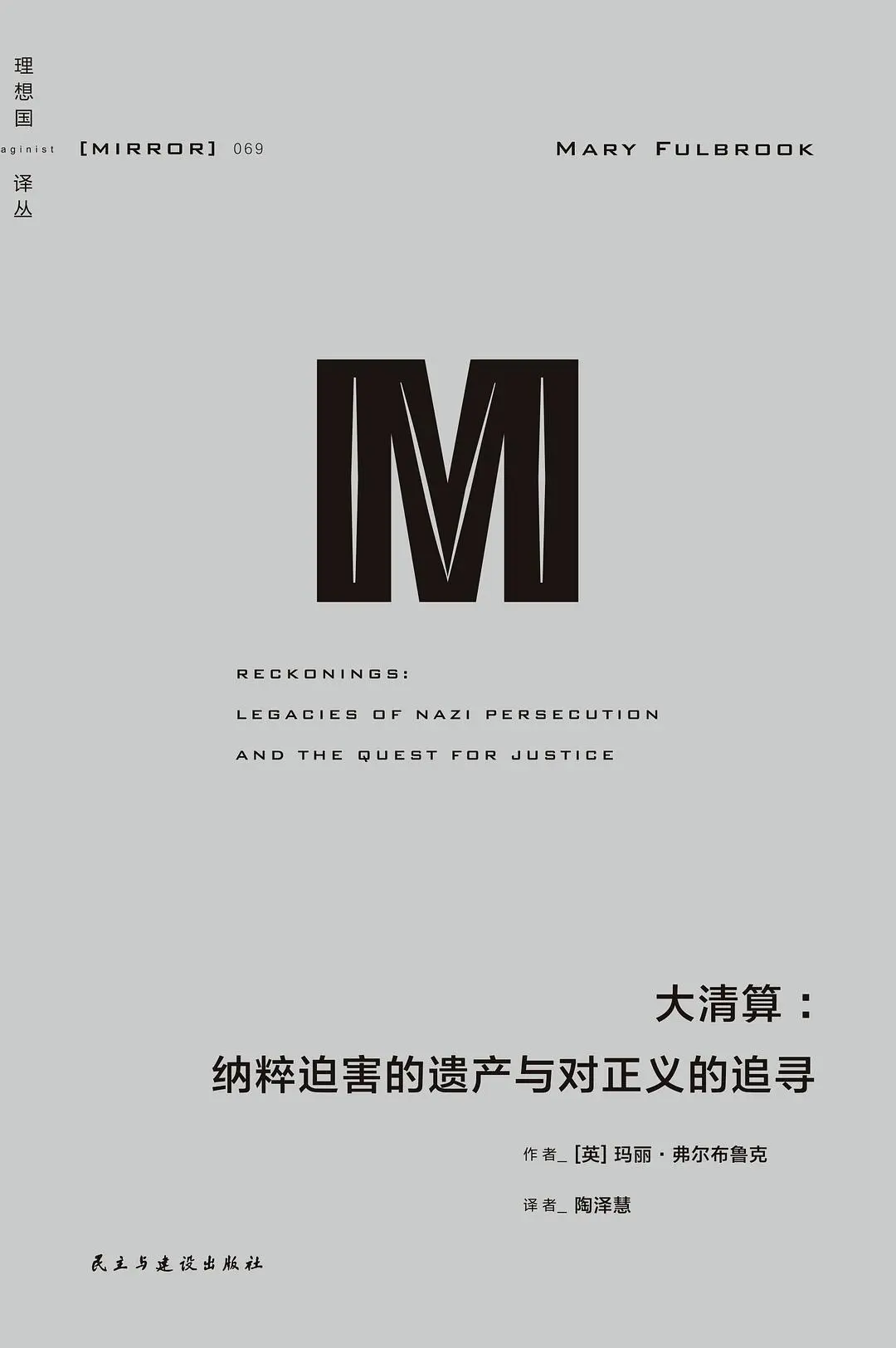
无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后代,还是作为加害一方的前纳粹成员及其后代,恐怕都很难真正直面与走出这段历史。纳粹的这段历史始终是笼罩在德国乃至欧洲上空的乌云。加害者及其后代以各种理由为自己与其祖辈在当时的行为进行辩解,否认个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而幸存者及其后代由于种种原因而保持沉默,导致战后整体的生存处境比加害方要糟糕得多。所幸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由于代际更新等各种因素,对纳粹德国的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可以肯定的是,反思纳粹德国的根源,力求避免类似政权的再次兴起,不仅对于德国与欧洲有现实的意义,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都有毋庸置疑的价值。在当下的世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是特别让人忧心与警惕的走向。纳粹德国的历史并不久远,选择对那段历史进行遮蔽或是遗忘,反而更可能造成历史的重演。
二
读完《大清算》之后,产生的疑惑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参与这场大规模针对特定种族的大屠杀,除德国之外,其他当时被占领的国家如波兰与罗马尼亚也均有深度参与,觉得有必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下德国二战前后的历史。正好之前买了不少理想国系列的译著,其中就有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剑桥大学历史学讲席教授)的“第三帝国三部曲”,分别是《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战时的第三帝国》,于是就转而去阅读这三本大作。
在《第三帝国的到来》中,第二章“民主之殇”描述的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状况。魏玛共和国在历史书上获评甚高,但它从建立到覆灭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在俾斯麦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瓦解之后,民主共和制作为替代的建国方案而出现并得到践行。然而,民主共和制在彼时并未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治势力,都不遗余力对它进行攻击,人们对强大的帝国怀揣梦想,更倾向于实行强人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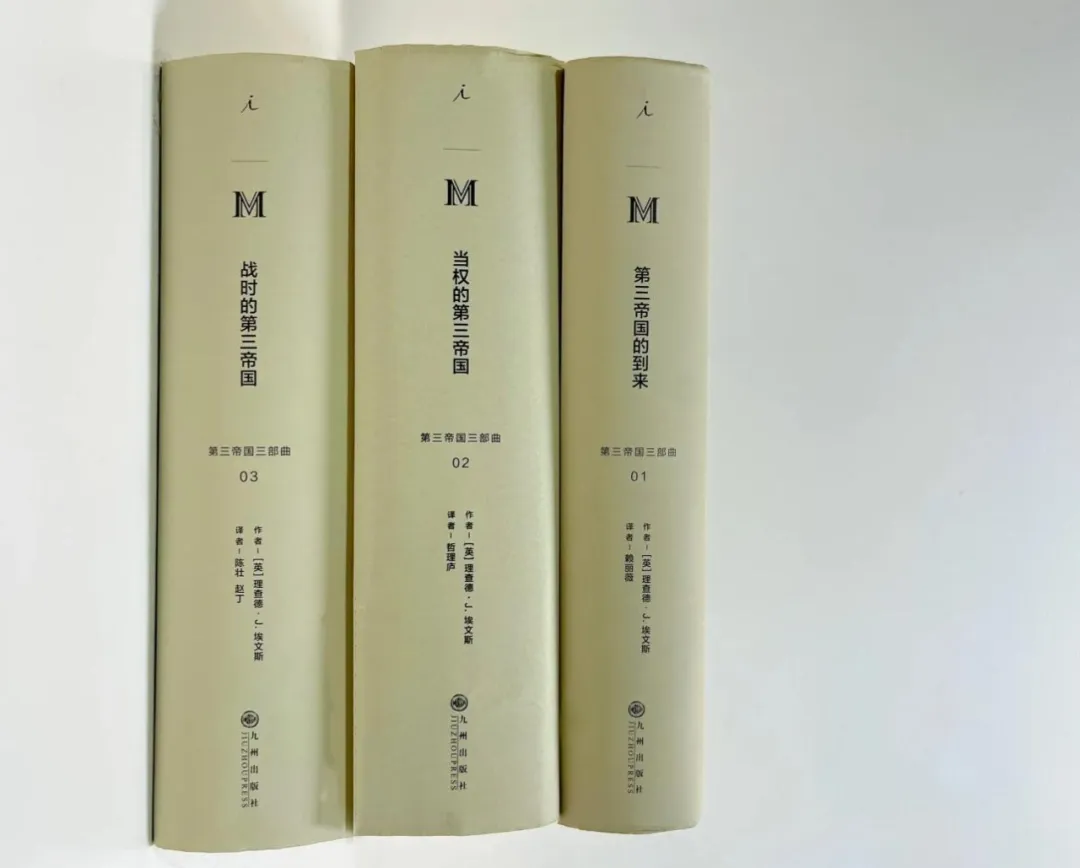
立足于专业的角度,法律圈历来在对魏玛共和国覆灭原因进行探究时,会特别强调其宪制构造的缺陷,尤其是魏玛宪法第48条关于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导致国家元首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疑问在于,如果没有第48条,以及宪制结构设计中的缺陷得到弥补,纳粹就不会在彼时兴起吗?
将纳粹的兴起主要归咎于魏玛时期宪制存在的缺陷,或者归咎于德国自身的文化与民族性,抑或推诿给特定时期的政治历史环境,可能都把问题给简单化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与在社会中寻找“替罪羊”群体,这样的现象在二十世纪以后各国的历史中都不鲜见。每逢全球性的经济下行,极端与排外情绪往往就会在全社会中流行开来,而极端右翼的政治叙事相应地会对社会各阶层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如何防止或是破解这样的历史怪圈,无疑是当代政治亟需解决的重大命题。
三
在《战时的第三帝国》中,我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一个是宾丁,另一个是梅茨格尔。这两位都是非常知名的刑法学家。在国内刑法学圈,大概没有学者会不知道这两位德国学者,甚至于法学专业的普通学生,但凡在刑法理论方面有些根基的,也大多都知道这两位。
其中的宾丁,作为刑法学中著名的规范论的提出者,明显是一位精神纳粹,尽管他在1920年就去世。他和另一位学者Hoche在1922年合作出版的《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中译:《赋予毁灭“生命无价值者”的自由》。在该书中,两人共同提出,国家应赋予医生“毁灭无价值生命”的自由,即国家与医学共同决定哪些生命“不值得活下去”,并据此执行“仁慈的死亡”。之后,纳粹当政期间推出T4计划,也就是对那些被认为没有价值的生命实施强制的“安乐死”(实质是谋杀),显然就与宾丁在书中倡导的理论立场一脉相承。
另一位梅茨格尔,我手头还有他在30还是40年代出版的一本德语花体字版的《刑法总论》。梅茨格尔积极参与纳粹期间的刑事立法,曾经制定对民族共同体相抵触者进行严厉处罚的刑法规范,这项规定主要不是针对特定的行为,而是针对个体的生活方式与个性倾向。相应的刑法规范用语非常含糊概括,导致犯罪处罚范围的边界极不明确,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梅茨格尔在这份法律草案的前言中指出,这项法律将被施用于 “失败者”“道德沦丧者”“犯罪者”以及“逃避工作者”。亏得这项刑法规定基于当时的外交需要没有施行,客观上未导致进一步的更大的罪恶。
这项刑法规定具体的内容为:“下列人群都属于与民族共同体相抵触者:(1) 任何人,如果依照他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来判断,他通过自身努力也无法达到民族共同体的最低要求;(2)任何人,(a)如果他逃避工作,举止轻浮,并由此过着一种对集体毫无用处、目无法纪或挥霍无度的生活……,或者(b)如果他极有可能犯下情节较轻的刑事罪或极有可能酒醉滋事,并由此严重渎职,不能维护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存在,或者(c)他因脾气暴躁、 耽于争执而持续地破坏集体和平;(3)任何人,据他们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来判断,他的自然倾向将导致他犯下严重罪行。”
这两位德国刑法学者的经历再次表明,走单纯的法律技术主义的道路非常危险,因为这意味着,法律技能与知识可以为任何政治目标服务。不只是法律,其他专业也是如此。纳粹当政期间,很多医务人员实施过更为不堪的行为,包括T4计划的具体实施与推进,当然还有后续大规模推开的毒气室以及严重违背伦理的医疗实验,都离不开医疗专业人士的积极参与。
缺乏起码的人文素养,加上专业的自以为是与傲慢狭隘,还有盲信极端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导致很多专业人士都深度参与罪恶而不自知。对此,我脑海中油然浮现的是韦伯的那句话: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我不是要否认制度本身的罪恶,很多时候制度有问题确实是第一位的,但不能由此否认个人在其中应负的罪责。没有灵魂的专家,有更大的可能成为恶的为虎作伥者,这不是一句“听命于人” 或“技术中立”可以辩解的。
四
很多人或许不了解,纳粹政权的有计划灭绝行动,最初就是针对本国被认为无用之人的灭绝开始的。因为纳粹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是从个体是否对社会或民族有用的角度,来决定他/她有无生存的价值与必要。与此同时,纳粹对东方人极度歧视,认为包括斯拉夫人在内的东方人都是劣等民族,就该灭亡,以便给雅利安这样的高贵种族腾出生存空间。所以,与西部战场不同,在攻占东部包括波兰与苏联领土的过程中,纳粹德国军队除了常规的军事举措造成的伤亡,往往会启动大规模蓄意的屠杀,既针对战俘,也针对包括妇幼在内的平民,动辄就屠杀几十万人,对象并不限于犹太人。
个人是否只有对社会或对民族有用才有生存的价值?国家是否有权决定一个生命的有价值与否?在当代,相应的问题如果还需要争论,真的是挺可悲的了。不止如此,有的人去支持与赞美要对自己实施生理灭绝的政权及其政治立场,按那种政治立场,自己和家人连小命都保不住,连生存于世的资格都没有,还有比这更为可悲与黑色幽默的吗?
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将保护人性尊严与基本人权放在第一条,正是基于对纳粹历史惨痛教训的吸取。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 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基本法》第一条被归为立法上不可修改的条款,“这些条款的不可修改性旨在确保宪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政治体制的稳定性,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从9月到10月,经历稍显漫长的阅读旅程,对埃文斯“第三帝国三部曲”的阅读终于快接近尾声,只有第三部《战时的第三帝国》还余下一章多的内容没读完,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看了书的结尾。
埃文斯爵士在书的结尾有这样的一段话:“第三帝国的遗产有着更广泛的受益者,远远不局限于德国与欧洲。我们每个人都有仇恨情绪与破坏欲望,哪怕程度很低,而第三帝国则以最极端的形式展现了人类仇恨情绪和破坏欲望可能达到的程度及产生的后果。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淋漓尽致地呈现了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威权主义最终的潜在后果。它展现了将种族三六九等区别对待会导致的后果。它也用最极端的形式抛出了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一刻会面临的道德困境——在我们被迫陷入的特定情境中,我们是选择屈服还是反抗,选择作为还是不作为。这就是为什么第三帝国不会彻底消失,虽然它的实体早已湮没在历史中,但它本身仍将继续引起全世界每个思考者的关注。”
对于埃文斯爵士的反思,我深以为然。第三帝国并非已经消逝的过去,它仍然以各种改头换面的形式渗透于当下,并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